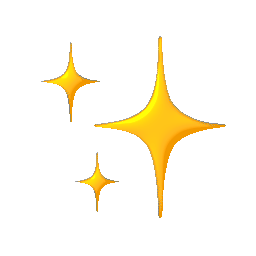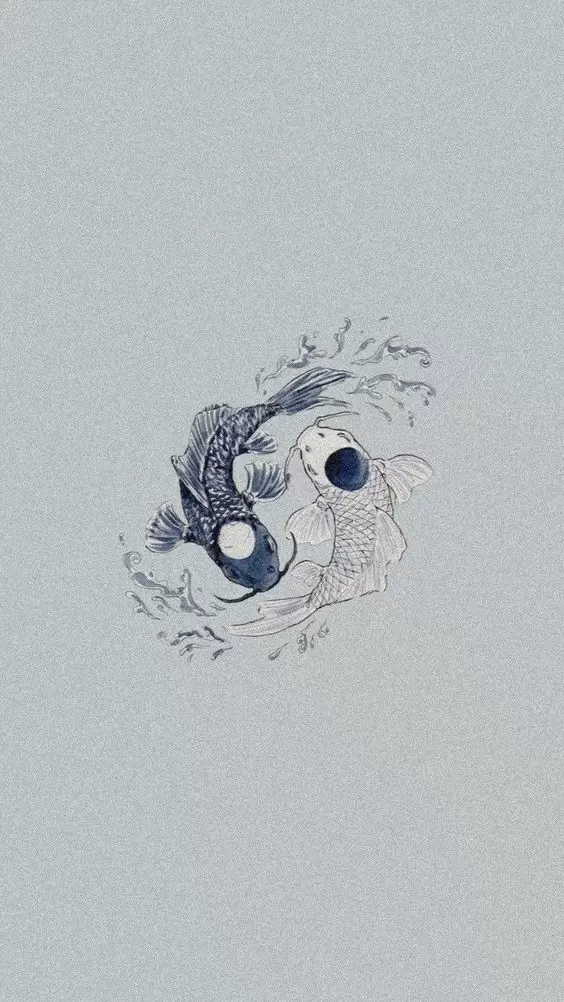
四柱猜測學的歷史淵源及發展概略
自古以來的歷代學者們,都想站在本年代的理論高度對「天」做出盡量合理的解說,然後找出某一社會文明表象所發作的理論依據。
咱們曉得,算命做為華夏民族的一種格外文明表象由來已久,任何帶有普遍表象的社會文明的發作都不能夠因偶爾要素俄然發作,都有著本身發作、開展和消亡的內涵規則可循。因而,不了解命理文明表象的起源,就無法窺破它的性質,也難以掌握命理文明活生生的精力命脈和內涵機制,就不能正確地恰如其分地估量這一文明表象所造成的或正或負的社會功用。
即然把算命做為一種格外的社會文明表象來研究。那麼,咱們就得從這表象的源頭說起。
第一節、夏商週年代的天命觀
所謂「天命」的意義,在不一樣的歷史階段有著不一樣的特定內容。在殷商曾經的初始氏族社會,因為出產力水平格外低下落後,出產數據和日子數據的極點粗陋和匱乏,每個氏族成員只需在初始的氏族集團中方能生計。任何人都日子在同一水平線下,底子不存在逾越氏族集體日子水平線之上的貴賤貧富表象。限於其時文明時化的程度,天然界在大家眼裡俱有無限的威力和奧秘不行降服的力氣。人類同天然界的聯絡好像動物一樣百般無奈地遵守它的威力。天然界中的風雨雷電、地震洪水、疾病猛獸隨時能夠吞噬人類的生命。而人類對天然界的知道只限於理性階段,即混沌蒼茫又奧秘恐怖。出於生計之需求,這個年代人類在思維生髮過程中沒有閒心也不能夠呈現盲目的對自個命運規則的深邃的考慮。因而,也不能夠發作描述自個命運規則的命理文明。人類只能把自個的命運消沉地百般無奈地交給奧秘恐怖的大天然,由此,又發作了對大天然的敬畏崇拜心理。

中化民族的先民們對命運對比盲目的考慮,那仍是在社會出產力有了極大開展,人類從天然界攫取的物質財富有了極大的積儲,同是地呈現了逾越氏族集體日子水平線之上的貴族。即歷史跨進奴隸社會往後的事。在這曾經,「命」在大家的心中並非指自個的貧富有賤,而是專指天然界對人類的製約。在他們看來,自個的死生及人世的萬物完全由那個奧秘莫測的「天帝」來操縱,因而「天帝」是到高無尚的。這從最牢靠的出土文物殷剋甲骨文中得到有力的證明:
「今二月,帝令不雨」。 《鐵雲藏龜》
「今三月,帝令多雨」。 《殷墟書契.前編》
「翼癸卯,帝其令風;翼癸卯,帝不令其風」《殷墟文字.乙編》
「帝令雨足年,帝使雨弗足其年」《殷‧事書契.前編》
不光是天然界刮風下雨是天帝的毅力,一起「天帝」也操縱全部社會人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玄鳥》
「厥初生民,時維姜……履帝武敏歆……載生載育,時維後稷」《詩經.大雅.生民》
商人的祖先是依從天命,吞了鳥蛋而生的。週人的祖先是踩了「天帝」的腳印而孕育的。儘管這是荒謬的傳說,但這個傳說卻蘊藏著中國先民們一個一起的精力崇奉,即他們的鼻祖都是「天帝」的子民。不但氏族的起源是「天帝」的毅力,就連人類社會的典章原則也是由「天帝」所決議,上至皇帝的人事組織、下到百官的職位設置,都要靠這位至高無上的「天帝」來組織,它操縱人的死生壽夭和吉兇。其實,這位至高無上的“天帝”,即是人世的皇帝。這種「天帝命結論」的觀念,實為控制階級神權政治的思維反映。夏商週年代政治上實施的是以嚴格的嫡長子世襲,庶子分封的宗法制為根底的分封制。經濟上實施的是國家公有的井田制。為穩固這種原則,他們又實施嚴格的等到級制。人的貧富有賤等等都是「天帝」的毅力所決議了的,是終身不變、千古永久的。只要敬天尊命,不逾法度便吉利和順;而逆天命無法度便自取其禍。
已然「天命」是不行改動的,全部都得遵從「天」的毅力,那麼大家何必算命,又有什麼理由來描述命理呢?所以在夏、商及西周初年這一天主命結論的天命觀佔肯定控制位置的社會環境和年代精力的歷史文明空氣中,命理文明底子沒有紮根的土壤,也不存在算命的社會文明表象。
在那個年代,大家在自我意識的領域中是一個漆黑蒙昧而可悲的年代。儘管咱們的先民們用自個格外的才智和勤勞的雙手發明了像司母戊方鼎這樣燦爛奪目的古代文明。可是威嚴嚴酷的奴隸原則剝奪了人對自我價值和自個命運考慮的權利,窒息了人的自我意識。大家在嚴格的以血緣聯絡而定的社會位置的社會結構中,一代又一代地重複著永不改動的人物。或許偶爾他們也考慮自個的命運,但是每逢這時,他們只能把木然無神的目光轉向冥冥的天穹。
第二節、春秋戰國時期,人類對命運的鬥膽探究及陰陽五行學說的建立
中國歷史上,春秋開端直至漢朝的建立,是一個大動盪、大分解的歷史時期,國家的經濟原則和政治原則都發作了底子的改動。井田制的破壞,直接動搖了政治上以血緣聯絡為根底的宗法制的分封制。格外是農奴的解放,一般布衣鼓起為地主,連商人也憑手中的權利參加國家的政事;分封的諸候為了擴張自個的實力互相爭霸,大力網羅宗法血緣聯絡以外的人才,乃至是奴隸身世的人,如赤貧到為人趕牛的寧戚憑才華被齊桓公拜為上卿,貧窮潦倒的百里奚憑謀略被秦國拜持平,開了老大眾也能當大官的習尚。進入戰國,「遊說則范睢、蔡澤、蘇秦、張儀等,徙步而為相;徵戰則孫臏、白起、樂毅、廉頗等,白身而為將。」(趙翼《二十二史札》卷二)。至於在社會改變中有的貴族從社會上層降落到社會基層更是常事。這些政治、人事原則的激劇改動,尤其是自個命運的大起大落以及時人對天象運動規則的初步掌握暨天然科學的開展和前進,發現「天象」和人事不一定具有必定的聯絡,這就不能不發作這樣的疑問:已然人的窮富有賤是「天命」都規定好的,亙古不變的,那麼和皇帝聯絡最接近的幾十顆血淋淋的國君的人頭何故落地?而窮戶大眾又反而能出將入相?這無疑是給長時間以來在大家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天命論」當頭一棒。必定導致時人對「天命論」的崇奉危機。反映在文學上也就呈現了不少咒駡「天命論」的詩章:「天主板板,下民卒癟,出話否則,為憂不遠。」詩經.小雅.節南山》

「天命反惻,何佑何罰。」《楚辭.天問》天上的天主是如此地非不分,喜怒無常,邪僻乖戾,恣意降災於人,人世的控制者是這樣的糊塗無能,沒有誠信,這又怎麼能取信於民呢?有些人不再信任冥冥中的天主,放下血緣決議命運的觀念,開端從人的本身尋求自個命運的普遍規則。
人的思考知道,總要遭到已有常識的約束。那麼供給給剛從漆黑的天命觀的縫隙中探出面來研究自個命運這個新課題的思維資料又是什麼呢?陰陽五行學說即是在這種歷史和社會的大佈景下應運而生。
最早提出人類日子一切必要的五種底子物質的是殷周之際的箕子。 《尚書.洪範》中記載了箕子關於五行之數的話後又說:「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是曲,金曰從革,土曰作物穡。潤下作咸,炎上作苦,鹹是曲作酸,從革作辛,作物穡作甘。
箕子的五行學說仍沒有完全跳出日子之需的圈子,卻是西周末年的伯陽父在箕子的基點上往上蹦了蹦,摘到一科學的果實。他是中國古代陰陽五行學說的倡導者,關於五行,他說:「先五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萬物。」伯陽父把大家日子中離不開的金木水火土五種細緻物質作為國際的本源,是其它全部物資的基始。正是因為這五種不一樣的物質互相連結才生成了萬物,顯然,伯陽父妄圖用物質本身來闡明客觀國際。
五行說被高度抽象化後,基實質不是構成國際萬物的底子元素,而是物質的五種底子形狀。金木水火土只是這五種底子形狀的代號。拿今日的話來說,金是固身形,水是液身形,火是氣身形,木是等離子態,土是歸納態,土容納全部,可被稱為「第五態」物質。國際是動態的國際,而物質的運動必定導致此一物質和彼一物質之間的形狀的變換,古人是用五行的生抑制化來闡明這一道理的。天然界陰陽互相效果發作了五行,五行相互效果則發作了萬事萬物無窮無盡的改動。
進入戰國往後,跟著陰陽五行說的鼓起和六合天然、生命形狀、社會人事同源同理,同步效應的世界觀的初建,不少學者以天然命結論來轉換孔子的天帝命結論,並清楚指出人的存亡、壽夭、貴賤、貧富等都是「天之所禀」的天然之數。這是中國古代命運觀上的重要改動,它的積極效果是對其時以宗法血緣定貴賤的封建制的無窮衝擊,消沉方面則是進一步否定了後天自個盡力的效果和含義。如《淮南子 .謬稱訓說:「人無能作也,有能為也,有能為也,而無能成也。為之為,天成之。終身為善,非天不行,終身為不善,非天不亡……故正人順其自然,在已者罷了矣……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這一觀念,《列子.力命》篇還煞費苦心的將「力」與「命」虛擬為兩自個。
這段文章的粗心是說,「力說,人的貧富有賤,窮通壽夭,都是後天盡力的成果呀!這是我所能做到的事。命說,即然如此,那麼彭祖的才華比不上堯舜,而他卻能活到八百歲;顏淵的才華高於世人,而只活了三十二歲;孔子的道德無疑高於諸候,卻貧窮終身;殷紂王極無道德,卻高居帝王之位;季札是吳國的賢士,卻一向無官;而霸道的田桓卻佔有整個齊國;伯夷叔齊都賢,最終卻餓死在首陽山上;魯國的季氏雖惡但巨富,你要是有才能來改動這全部,為什麼不去改動它呢?力命篇》完全否定人的後天的主觀能動性。片面強調消沉地「聽其天然」的命運觀,這是與高度極權控制的整個封建社會原則和文明相適應的。經典的正統文明對「聽其天然」的消沈命運觀的分析遠不止以上所述,但這些資料底子上道出了中國古代消沉落後的舊命運觀的底子內容。

第三節、 兩漢之際,四柱猜測學理論的初建及王充的禀氣說
如果說,西漢時期四柱猜測學理論的初建多形而下總結的話,那麼到了東漢王充禀氣說的創建,使中國的命學理論有了清晰的哲學根基。
王充承繼前人唯物主義觀念,主張氣的一元論,他以為氣是構成國際的本源,「萬物之生,皆禀元氣」(王充《論衡.言毒篇》),萬物不一樣的本源在於禀氣的不一樣,「因氣而生,品種相產」(王充《論衡.物勢篇》),這本是前進的唯物主義天然觀,但他機械地將天然界的必定性用來類比社會人事,他儘管是個偉大的無神論者,但他的稟氣說又構成了奧秘的宿命論的天然命結論。在他看來,決議一自個壽夭、貴賤、貧富、禍福的東西,是開端“在母體之中”禀受的“天然之氣”,這在一自個取得生命之時便已構成了,就像草木的形狀良莠決議於種子,鳥的男女強弱決議於鳥卵一樣,人的命運所包含的全部都決議於開端禀受的「天然之氣」。他以為人的壽數的長短,取決於胚胎在母體所禀受的氣的厚薄,「夫禀氣厚則體強,體強財其命長;氣薄財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短壽。人的壽夭如此,命祿也一樣。所謂「命者,貧富有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王充《論衡.命義篇》)它不決議於人的才華賢愚等後天要素,決議於人開端偶爾所禀的天然之氣。天然之氣有厚薄之別,所稟之氣,厚者命貴,所禀氣薄者命賤。因而每自個的命祿是先天之氣注定的。 「命當貧賤,雖富有之,猶涉禍殃矣。命當富有,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王充《論衡.命祿篇》)所以命貴的人和他人一樣學習,只要他能當官;和他人一樣當官,只需他能步步高升;命富的人和他人一樣經商,唯有他能發財,命賤的人則做樣樣事都徒勞無功,白白遭罪。吉兇也如此,「凡人授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兇矣。」(王充《論衡.命義篇》)命當富有,能夠逢兇化吉,常安不危;命當貧賤,禍殃並至,常苦不樂,這是人的任何盡力都無法改動的。
王充的天然命結論的理論是針對董仲舒的「天命論」和神學觀而發的。他的「氣一元」所說的唯物主義觀念對「天命觀」當然是個強烈的抨擊。
從殷周之際讓咱們的先民們望而生畏的“天帝命結論”到春秋戰國時期陰陽五行說的建立,又從兩漢之際的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到王充的“天然命結論” ,無疑是人類知道史上的一次騰躍。但是任何一種普遍性的社會文明款式的理論的構成,都不能歸之於某一自個的效果,都有著深厚的歷。